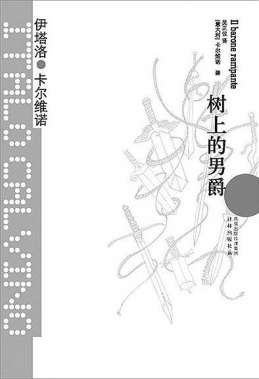
《树上的男爵》封面
化石空白时期的人类祖先,由消退的海洋抵达陆地,又在古猿到人的演化过程中脱离茂密的森林束缚,从树干上爬下来学习直立行走。毫无疑问,直立行走扩大了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强化了肢体分工,是转变成为“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或许,纵使千百万年沧海桑田,人类潜意识梦境中渴望重返森林大树的记忆仍会不时袭来,因此总有特别的人在特别的时刻提醒你,“树顶上看到的世界是如此不同,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小说《树上的男爵》中以超越尘寰的视角,虚构了12岁的男爵柯希莫,为了逃离父亲的权威和控制而爬上了大树,从此在树上以超乎寻常的生存智慧度过大半生,在65岁时攀住路过的热气球而消失了的现代神话。柯希莫在树上构建了一个生态王国,以搭建的树屋为居,以打猎和钓鱼为生,并且和恋人在树上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柯希莫坚持生存在树上,就连我们也认为这一行径是对文明社会的叛离和对原始生命野性回归的象征,因此某种程度上,柯希莫更像是大家内心深处渴望成为的那个人——摆脱重复着和模仿着的人生轨迹,找回自由的状态和价值。
但卡尔维诺写道:“想要清楚看见地上的人,就应该和地面保持必要的距离。”显然,柯希莫的行为与这句富含哲学意味的话语是要割裂开来对待的。凭借超乎常人的坚定信念,柯希莫拥有了独特的存在方式,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仍旧在没有干扰和限制的生活中做着自己。而正是由于这种与地面的距离,又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角度来观察别人。这种被观望者反观他人的读者视角,又让我们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和反思:究竟哪种状态下的存在和心灵才是自由的?哪种情境下的情感和认知才是真实的?失去了爱人的柯希莫迅速衰老了,他面对的更多是孤独无依,更多是风吹雨打,可为什么他宁愿死守着自己的边界,却不肯从树上下到地面重返尘俗?这种偏执的倔强是对追求自由的终极坚守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通常,寻找答案的过程比答案本身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不妨把目光转移到卡尔维诺的另外一本书《看不见的城市》上,或许在森林与城市间看似矛盾、疏离的关系下可以看出一丝两者紧密相连的端倪,便也能对柯希莫的“固执”有所理解。《看不见的城市》里有55个被虚构出的意象城市,以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汇报的方式对此分别描绘。沿着如同聚集55面体的巨大圆球的棱角边缘前行,城市俨然就是世界的微缩。我们既可以在某一面体中找到似曾相识属于自己的城市,也可以发现令人艳羡的别人的城市。在被描绘的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中,或许因为某个细节与自己的某种特殊联系,从而让城市有了意义,让存在有了价值。
瓦尔德拉达是一对镜像城市,一座在湖畔,另一座则是湖中的倒影,湖畔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倒影中完美重现,因此瓦尔德拉达的居民会格外审慎自己的一举一动,即使是杀人凶手也要力求在现场的形象冷静清晰,拥抱爱人时手臂的姿态唯美可人。可如果你有仔细观察镜中影像的经历就不难发现,虽然像和物是左右对称且大小相等的,但是镜中的像是虚像,只有光照射到物体再经过反射到人的眼睛才能被看到。瓦尔德拉达的镜像之城就如同王阳明口中的“此花不在你心外”,被感知继而内心存在的才能成为意义的源泉。而“镜子外面似乎贵重的东西,在镜子中却不一定贵重”,卡尔维诺笔下的瓦尔德拉达承载着有与无、相似与冷漠、依存与独立,很难说两个城市谁更自由,谁又在模仿着谁。
不知道是否因为柯希莫看尽了树下人生的重复和模仿,所以卡尔维诺造出了另外一个城市——埃乌特洛比亚,全市居民如果厌烦了这里的一切,就可以决定搬到邻近的空城开始新的家人、新的职业、新的消遣。就像艺电公司出品的游戏《模拟人生》一样,玩家通过设定市民角色开始自己的创意生活,而在创意之中又会对真实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埃乌特洛比亚居民的生活显然是多姿多彩的,但卡尔维诺说“我以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四处游荡流亡,其实只是掩饰至今没有找到愿意驻足的地方”。与不越雷池一步、坚守在大树上的男爵相比,充满无数未知可能性的新生活总是值得期待的,但期待本身也是另一种局限。
有时候,我们假装无情抛下烦弃渴望改变现状,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卡尔维诺在书中写道:“死亡,就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柯希莫去世后,他所栖居的翁布罗萨森林被砍伐殆尽,传奇世界也随之消逝,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怅惘。“柯希莫下树,小说也该结束了,然而卡尔维诺不让柯希莫下来,柯希莫就不下来。”柯希莫永远活在了那个“平行空间”里,从人群中被分离出来的他被赋予决定所有事情的权利,但权利总是伴随着义务,柯希莫也必须捍卫在树上的尊严。
现实世界与自然世界,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在与世界产生关联的一刻,就不存在赢者,而世界的意义也在世界之外。在地面生活久了应该爬到树上看一看,而在树上生活久了也该下到地面看一看,因为世界是如此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