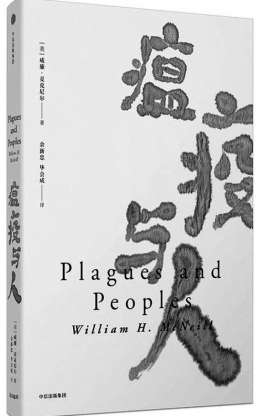
《瘟疫与人》封面
四年前风靡社交网络的“冰桶挑战”,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它是为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亦称“渐冻人症”)而进行的募捐活动。“渐冻人症”这样的罕见病,全球有7000种。在近年来对罕见病立法以期保护罕见病患者权益、探讨特效药进出口的法律规制的背景下,读《瘟疫与人》这本书,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瘟疫与人》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大师,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本书是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其他著名作品还有《世界史》《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人类之网》等。《瘟疫与人》最早出版于1976年,一经出版在史学界就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学者从医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兴衰的秘密。
探讨疾病与历史的关系,无疑是一条学术险道。在此之前没有人系统梳理疾病的历史,即便有一些文献,也都是零碎和片段式的。为了撰写本书,麦克尼尔查阅了全球大量相关史料,并且向医学领域的专家虚心求教。《瘟疫与人》的学术价值与治学精神,非一般学者能企及。
按照编年史方法,《瘟疫与人》分为“狩猎者”“历史的突破”“欧亚疾病大交融”“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跨越大洋的交流”“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六个章节。书中,尤其对于世界上曾经大面积传播的瘟疫,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作为开拓性的史学著作,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程指出:“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虽然至今距离本书首次出版过去了40多年,可是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耳目一新。
《瘟疫与人》一书中,从疾病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往往与之前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过程中,1520年科尔斯特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缘由,麦克尼尔认为关键是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见怪不怪的致命杀手——天花。《瘟疫与人》中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斯特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个晚上,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征服了印第安人。今天,这一观点已被很多人所接受。
类似的例子其实很多。公元前430年至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人之战难分胜负,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政治趋向。再如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得两万法军丧失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麦克尼尔认为:疾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要素之一,无论认不认同,这都是客观的存在。
曾经有几次席卷世界的严峻疫情,把人类及其创造的文明推向了风口浪尖。其中,黑死病是最令人恐惧的疾病。历史上因黑死病死亡的总人数高达2亿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黑死病对于欧洲的历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至今欧洲人谈起黑死病,都心有余悸。
在中外历史上,除了噩梦般的黑死病影响着历史进程,还有其他一些疾病,也同样发生过巨大的“威力”。天花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患上这种疾病,如果大难不死,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天花”由此得名。我国在清朝时期,很多人都无法逃脱天花疾病的魔掌,比如顺治、同治两位皇帝,都曾感染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印痕……
史料记载,明朝末年中国北方大旱,导致大面积的饥荒,饥饿难忍的老百姓四处寻找老鼠充饥。饥荒年代,老鼠也找不到可食用的粮食,老鼠体质变弱,其自身携带的病菌格外多,干旱而高温又促进了鼠疫杆菌的繁殖。1644年,仅仅一年的时间,北京就有30%的人口被鼠疫夺去生命。如此严重的疫情,直接动摇了明末的统治根基。
最后是艾滋病。麦克尼尔在撰写《瘟疫与人》一书时,这种病毒还鲜为人知。1981年6月,美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截至目前,全球艾滋病人口已经超过3600万之多。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8至9年,然而,医学界目前无法获得治愈的“神药”……不过这些疾病的流行也让流行病控制的立法成为法治领域一道特别的景观。
历史上广泛传播的各种疾病,夺走的人口数量远远多于战争。近一百多年来,现代医学技术虽然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但是麦克尼尔提醒人们,不要过于依赖现代医学,因为技术并非无往不胜。提升疫情的应对能力,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考验着社会的治理水平,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超出我们的想象。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